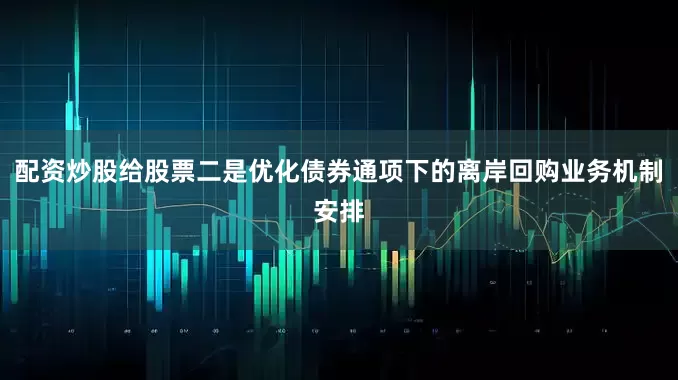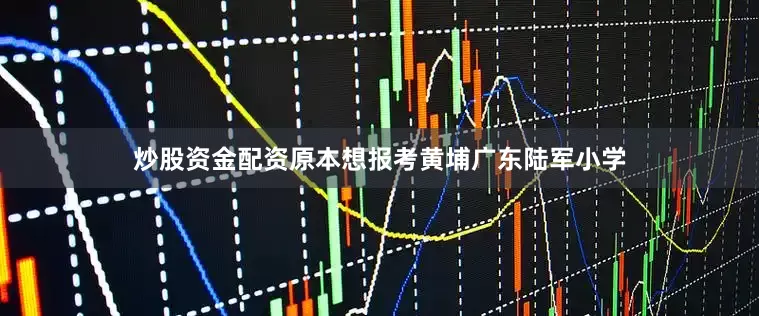
在辽沈战场被俘的那一天,范汉杰留着一副浓密的大胡子,眼睛却并不慌张。照片里,他站姿工整,像是仍在迎检的军官。问话时,工作人员例行登记家庭人口,他先装出一副愁苦模样:“吾一人死不足惜,一个班加一个排亦无生计矣!”众人不解,他才笑着解释:“老婆一个班,子女一个排,若我不测,老婆子女何以为生。”笑声在紧张空气里漾开,仿佛一根冷线被悄悄拨断。这个会在战俘管理所里“报告大便”“写遗嘱”逗乐同狱者的人,后来被关押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整整十二年,剪去多年的长胡须,写日记、看书,读到高等代数、微积分,也下功夫啃辩证唯物论和社会发展史。他认真地配合改造,像训练班里一丝不苟的学员。1960年,他被特赦,列入第二批获释战犯之中。

书斋里的战犯与制度背影
新中国的战犯管理所并非仅是铁门与规条,也是一间间临时的课堂。范汉杰获释后,被安排到北京市郊区红星人民公社的园艺队劳动锻炼,期满回京,与其他第二批特赦人员一起,在中南海国务院办公室受到周恩来总理、陈毅副总理的接见。他随后担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委员,被分配在军事组,专事审核东征、北伐、抗日方面的稿件。1962年至1966年,他审阅了数十万字,亲撰材料亦有数万字。对于历史研究,这一批走出战场的亲历者,把个人记忆磨成材料,成为难以替代的底本。

“特赦”并非轻率之举。它既依据个人表现,也映照政治氛围:对旧制度军政人员的改造与团结,在当时被视为稳定新政权社会结构的重要环节。范汉杰的轨迹,恰好可以作为这个政策意图的注脚——一个被俘之人,以合作与勤学换得再度进入公共生活的机会,并在文史整理上继续“服役”。
“老大哥”的由来

把镜头拉回二十年代的黄埔岛。黄埔军校一期学员多是意气方刚的青年,二十出头,正合“少年将校”的典型形象。但范汉杰报到时,已近三十岁,当时他甚至身居粤军第六路司令的高位。按常理,他完全可以沿着军界路径继续上升。偏偏他出于对孙中山的仰止和对革命的认同,放下在军中的“现成局面”,报考黄埔军校第一期,被编在学员第四队。这位“年龄最大”的新学员在同侪中很快被称作“老大哥”。
“老大哥”的身份还不止一个。学校正缺地形学教官,他又恰恰擅长测量,于是干脆由校方请他上讲台。他既是学生,又是教官,这样的双重身份在黄埔历史上并不多见。与多数“从零打基础”的黄埔同学不同,他读过专业、带过兵、讲过课,带着成年人的冷静与不苟,和青年人的热度一起,在操场与教室之间穿梭。

从三角测量走入军旅
如果说黄埔是他精神上的再选择,那么更早的道路则是从一把经纬仪起步。范汉杰出生于广东大埔县三河镇梓里村,家境谈不上富裕,但书香不缺。父亲范之准曾任梓里公学校长,家里对读书格外重视。他先在西翰轩(今大埔仰文小学)启蒙,后入梓里公学。1910年,他与三哥赴广州,原本想报考黄埔广东陆军小学,却因不熟粤语,转入优级师范附属理科。第二年夏天,考入广东陆军测量学堂第五期三角科天文测量班,钻研得极为扎实,毕业后即任广东陆军测量局三角课课长。1918年,他出任援闽粤军总司令部军事委员,从此真正踏入军界。

这里有个制度的小注:清末民初的军政体系里,测量、地形、筑城与兵器配置紧密相关。拥有系统测绘教育背景的人,在参谋、教练与野战指挥层面都占有先手。范汉杰的后半生,无论在教官岗位,还是在战区指挥部,都能看出这一“专业之根”。
德国课堂与中国战场的互证

1928年,他远赴德国深造,为期三年。前半段在德军下级部队轮训,从排、连、营的野外演习到战斗教练,一项项实操过手;随后回到柏林,在步兵、炮兵、骑兵、工兵、辎重兵等五所专门学校见学;末段进入高层课程,研究欧洲战史,以及战略、政略与军制。这段经历带来的不只是“见世面”,更是对现代军队训练方法的整体认识。
“九一八”事变爆发,同时父亲去世,他随即回国。不久又患上吐血症,赴庐山疗养。休养仍不松懈,他把德国战斗教练的小丛书与图解译出,由国民政府训练总监部印发全国各军作为练兵资料。对一个把“教练”和“战术”都当作硬功夫的人而言,讲义不是纸面游戏,而是战线另一端的“兵之日用”。

福建风云与立场再选
1932年1月,范汉杰任十九路军参谋处长,随军参加淞沪抗战;随后十九路军入驻福建,他兼任闽省绥靖公署参谋处处长。1933年11月,李济深、蔡廷锴、陈铭枢等率十九路军发动“福建事变”,意在联合共产党、反对蒋介石,同时对外抗日。当时十九路军扩编改名为人民革命军第一方面军,蔡廷锴为总司令,范汉杰任副参谋长,并兼参谋处处长,负责大量军事事务。

蒋介石旋即集中兵力围攻。蔡廷锴派范汉杰赴厦门,与蒋鼎文(为第三路军总指挥)商洽对十九路军和平改编,以期保存部分抗日力量。变局往往在无人的一瞬完成:范汉杰离开后,十九路军即被击溃,余部改编。此后,他开始一意追随蒋介石,被调入胡宗南的第一军,晋升少将军衔。与蔡廷锴等人的路径相比,这是一次关键的转身。福建事变的参与者中,有人流亡,有人隐退;而范汉杰转而在国民政府的军事体系内再爬坡,后续履历也随之完全改写。
横向看同辈军人,三十年代许多人处在“抗日”与“内战”的交错之间——对外的战争需要专业与纪律,对内的政治风浪要求站队甚至妥协。范汉杰既有专业主义的一面,也有政治抉择的一面。两者相互拖拽,让他的履历呈现出明显的断点:福建之后,便是全面抗战与内战序曲。

从副总司令到锦州被俘
全面抗战爆发后,范汉杰的职务不断上升。到了解放战争,他已任陆军副总司令。1948年9月,辽沈战役打响,范汉杰以东北剿总副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的身份坐镇要地。辽沈是决定国共去向的大决战之一,锦州之失,成为整个东北板块倾塌的转折。范汉杰最终在锦州被人民解放军俘虏。站在战役尺度上,这是一枚关键棋子的倒下;对他个人而言,亦是从军旅巅峰遽然跌入谷底。

黄埔气质的两种面
黄埔出身的军人常被为两类风格:一种是骁悍敢战,重情重义;另一种是偏向组织、训练与参谋工作。范汉杰恰像把两者缝在一起的那种。他在黄埔既为学员又为教官,毕业后却并未靠资历走捷径,反而“从头再来”,自排长做起,历任连长、旅长。这种逆向“回炉”的选择,与他此前已任粤军第六路司令的资历形成鲜明反差。这样的反差既来自理想主义的驱动,也源于他对专业能力的自信——在战术与训练领域积累越深,越不惧从底层岗位往上再走一次。

在制度层面,这也折射出黄埔军校的一个特点:它重塑的不仅是军官的知识结构,更是军官的政治身份。对三十岁“高龄”的学员来说,校旗之下的共同体意识可能比升迁更有吸引力。范汉杰在同学口中的“老大哥”,多少就是这两种黏合的产物。
幽默与坚忍:功德林的另一面

被关押在功德林的十二年,范汉杰以积极态度配合改造,保留了写日记与学习的习惯。读到数学与哲学,既像一种补课,也像在给自己另辟精神阶梯。那些“报告大便”“写遗嘱”的段子,让他成了功德林里的“名人”。这一面并非轻浮,而是一种老兵式的解压。比起怨懑,他更习惯用调侃渡过不确定的日子。
家国之外的家事

若将视线从战场挪到家庭,会发现他的“一个班一个排”并非虚言。范汉杰有一妻一妾。妻子童绩华为广东大埔人,生子女九人(一说七人);妾室林剑锋为福州人,是民族英雄林则徐的重孙女,生子女三人(一说四人)。子女多有成就:林剑锋所生之子范大胜,曾任美国通用汽车公司主任工程师、美国陆军车辆研究中心顾问,1985年出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高级顾问,还曾赴清华大学、重庆大学、华中工业大学及长春汽车制造厂讲学。女儿范大蓉在南美任工程师;儿子范大潮在台湾基隆港务局工作;一人在台北叫范大英;还有一人在梵蒂冈工作;其余子女也都大学毕业(细节不详)。从地域到行业,这个大家族几乎将近代中国人的迁徙路径与智识流动刻在了家谱上。
一座奇屋与乡土的回声

在家乡大埔,他还建了一座“火船屋”——“杰庐”。外形如火船头,在客家话语体系里,女人常被戏称作“船”,这种造型被视为犯了风水大忌。然而“犯忌”也意味着特别,杰庐因此颇有名气,吸引了不少游客。风水与建筑,民俗与个人审美,在这座屋子里打了个照面。对于一个长期在严整营房与冷峻司令部之间徘徊的人来说,这样的“标新立异”像是对乡土的一次幽默回应。
从广州到锦州,从课堂到指挥所

把分散的节点串起来:1911年夏,他进入广东陆军测量学堂第五期三角科天文测量班;毕业后任广东陆军测量局三角课课长。1918年成为援闽粤军总司令部的军事委员。1924年黄埔军校创办,他已是粤军第六路司令,却毅然报考黄埔,进入第一期学员第四队,并登上讲台教地形学。毕业后不靠资历,从排长做起,直至旅长。1928年前往德国见学三年,按连排营实习—五兵科学校见学—战略与军制研究三阶段进阶。九一八和父丧让他返国,吐血病又逼他去庐山休养,翻译的德军战斗教练丛书被国民政府训练总监部印发全国部队,成为练兵教材。
1932年1月,他任十九路军参谋处长,投入淞沪抗战;继而任闽省绥靖公署参谋处处长。1933年福建事变中,他为人民革命军第一方面军副参谋长兼参谋处处长,后因与蒋鼎文洽谈和平改编而离开前线,旋即十九路军被消灭,余部改编,他此后追随蒋介石,调入胡宗南第一军,授少将军衔。全面抗战中职位再升,至解放战争任陆军副总司令。辽沈战役时期,他是东北剿总副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,锦州陷落时被俘。

落幕与两岸的最后安排
晚年的范汉杰,已不复当年挺拔,眼神里多了风霜。特赦后,回到公共生活,谨慎而勤恳。1976年1月16日,他在北京医学院附属医院病逝,享年八十。骨灰安葬于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。后来,旅居美国的儿子范大胜返京,将骨灰盒中的一半携去台湾安放,于是他有了“埋骨两岸”的安排。一个人的命运在两岸之间分配安息之所,也像给那个支离的时代留下一则注脚。

意义与回望
把范汉杰与同时代数位将领横向对照,会看到一条别样的轨迹。与蔡廷锴、李济深那样在福建事变后走上不同道路的人相比,他更早做出回归国民政府军政体系的选择;与一般黄埔“少年英才”又不同,他在进校前已位至路司令,在校期间兼教、兼学,毕业后却自排连干起;与一些“学贯中西”的军官类似,他在德国的经历,最终变成一册册实用的训练教材。其间的逻辑并非直线:理想与现实、专业与政治、战功与失败,彼此拉扯,塑造了一个复杂的人。

辽沈之败并不能抹去此前的专业积累;功德林十二年的安静也未削弱他后来在文史材料上的价值。若说黄埔给了他“军人共同体”的身份认同,那么德国训练给了他“现代军队”的方法论;福建风云与辽沈败局,则让他认识政治力量与战略大势的真正重量。正如古人言:“人事有代谢,往来成古今。”从梓里村到黄埔岛,从柏林课堂到锦州城垣,这位“老大哥”的人生在大时代的浪头上被反复推搡,最终停在一张张经年泛黄的史料里。
可靠信息来源:

人民网——盘点建国后被特赦的知名人物及去向92015年08月26日
抗日战争纪念网——范汉杰2018-12-07

富腾优配-正规配资开户-安全配资-最正规的股票杠杆配资平台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